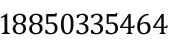文物是连接历史和未来一条生生不息的血脉,更是一方地域文化底蕴最有力量的见证——
发现:浙江10000年的文物辉煌
这是东方一片美丽的土地,长江和钱塘江共同雕琢出它10.18万平方公里的妖娆身躯;这是东方一个动人的神话,那点燃瑶山、汇观山的圣坛之火,那燃烧在德清窑、龙泉窑的不息柴火,曾令多少的朝圣者迷离。
谁不羡慕这耀眼的繁华和彻夜的喧哗?就连严谨慎微的考古学家也没能挡住它的诱惑,被它陶醉,为它痴狂。
30年风雨兼程,30年锲而不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经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他们手中的“洛阳铲”不断揭开古越大地荒草萋萋的历史尘封,使它曾经沧海桑田的面庞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田野上一群用心的探索者
驱车从杭州市中心向西北约13公里便是余杭区良渚镇,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却拥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良渚:美丽的水中小洲,“美丽洲”。1936年良渚人施昕更先生的一个发现,让这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字为更多人所熟知,良渚亦从此声名远播。
施昕更先生的这个发现,就是最终被考古学家以最早发现地“良渚”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2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广袤土地上,良渚文化在这方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了1000余年。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这是浙江考古学肇始的重要标志——自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首先在余杭良渚发现良渚文化至今的70多年间,经了旧石器时代的筚路蓝缕以及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的风风雨雨,复杂的社会结构、完备的礼仪制度,以玉器、漆器、黑陶为代表的卓越的艺术成就……
1955年,浙江对余杭长坟遗址的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良渚遗址范围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20世纪80年代初,以吴家埠发掘为标志,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神秘的良渚文化也揭开层层面纱。反山、瑶山发掘引起巨大轰动,并迅速掀起一股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研究的热潮。不久,汇观山、莫角山等重要遗址被揭示,良渚文化的研究又被推向新的高潮。
上世纪70年代,震惊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是长江流域史前考古的里程碑,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之一,轰动海外。7000年悠久历史,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当人们还在赞叹古越大地的悠久灿烂时,浙江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又让全国乃至全球考古界为之震撼。从旧石器考古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5万~10万年左右的“建德人”,到安吉上马坎、长兴七里亭、合溪洞遗址发掘,把浙江人类历史提前到80万年以前,再到近年来,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和命名,让浙江一次次成为全国考古学界的关注热点。
——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唱响的上山文化,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万年以前。上山遗址发现的水稻,将浙江稻作文明整整提前了2000年。
——在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千余粒稻壳与稻米颗粒。结合粒型的长宽比角度,可以确定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是一些经过人类驯化的古栽培稻。这一发现,使浙江的文明史又向前推移了1000年!
——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是继河姆渡、鲻山遗址之后,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的又一重要发现。
——“良渚古城”以其宏大规制,被考古学界称为“中华第一城”,是良渚文化的国都所在,同时将杭州的建城史提前了整整3000多年。
——遂昌好川遗址发掘,表明好川文化是一支分布于浙西南瓯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浙西南史前考古的重要突破。
——扑朔迷离的千年雷峰塔地宫铁函终于开启。五代鎏金纯银阿育王塔、唐五代鎏金铜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面对着一件件稀世珍宝,人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清脆的瓷之声,传来了悠远的历史回响;厚重的尘之土,掩埋了曾经的辉煌源头……2008年4月25日,中国青瓷历史在这一天被重新改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德清县博物馆,在德清县经济开发区龙胜村后的亭子桥发掘一处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窑址,首次出土大量高档仿青铜礼器和乐器证实,这是一处专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战国时期专门为越国王室和贵族烧造高档次仿青铜礼器与乐器的地点就在今日的德清。
瓷,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用自身的演进,诠释着时代的变迁:走过商周的漫漫长路,经历六朝的风风雨雨,见证大唐的伟大宏图,千年沧桑过后,今天依然光彩夺目。如果说瓷是参天历史大树上结出的硕果,那么龙泉无疑是一片理想的沃土。大窑枫洞岩窑址等一系列关于龙泉青瓷的考古新发现,让人兴奋不已。
给文物涂脂抹粉的美容师
从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到飞英塔、衢州孔庙、延福寺、胡雪岩故居等一大批文物维修开放,无不凝聚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的心血。
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在成为回忆,回忆如同梦想一般,在时间的积淀中,留下一串历史的足迹。等人们的脑子渐渐不好使的时候,回忆往往就需要有所依托,比如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一盏斑驳的旧油灯,或者一幢古建筑,如果它们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然后提醒着人们过去的存在和自身的渺小,人们就可以一头扎进去,陷入绵绵悠长的怀旧情绪之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怀旧情绪,也是人们认识历史,探索文明,追寻人类发展规律的过程。文保工作者用一连串的数字不但书写着考古所的历史、更为全社会构筑着浙江的文化基因“图谱”。
从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全省登记23804处不可移动文物,到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70427处,三代考古所专家引领全省文物工作者爬山涉水、走村串户、风餐露宿,先后进行了三次全省文物大普查,不断刷新着我省不可移动文物家底的总量,这里有他们的艰辛。
一处、三处、十三处、四十五处、五十九处……从第二批到第六批国保单位数量的不断快速增加,使浙江一跃跻身国保单位数量全国第五位,在国家遗产名录上不断镶嵌上“浙江”的名字,这里有他们的智慧。
从第二批浙江省级文保单位58处、第三批104处、第四批308处,不难看出考古所人行走在浙江大地上、上下求索全省近万年文明的脚步,攫取一个个历史的“金钉子”,编织起越来越生动清晰的浙江文物史迹网。
从2007年首次调查登记385处到目前发现登记1500处,不断刷新的运河遗产数量,向人们展示着浙江申遗的美好前景,用他们辛勤的劳动、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动着浙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脚步,为全省培养出一支熟练掌握世界遗产保护知识的专业力量,使全省遗产保护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与此同时,他们起草的《浙江省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草案)》等管理制度、规章,为科学构建我省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尽一份责任。一遍遍的修改,一次次的完善,400处文保单位档案的把脉会诊、数百处文保单位的维修方案、保护规划下的“诊断书”,这一切都是为给这些最珍贵的文物和文保单位建立起真实的档案,让每一次维修更科学、更严谨。
风雨兼程的30年间,文保专家和学者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开展了20余项文物保护专题研究,苦苦探究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文物保护工程示范项目的管理、新农村建设中的遗产保护等重点难点问题。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攻坚克难,不断拓展文物保护的领域,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含量。
因常年工作的需要,不间断地举办各类考古、文物保护培训班,培养遗产保护与考古、文物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广泛传播现代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理念方法,成为全省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孵化器”,支撑浙江遗产保护跻身全国领先行列。
无论是在1929年西博会工业馆旧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博会博物馆,风景秀丽的衡山南岳忠烈祠抗战精神展现,将钱氏功绩和吴越文化融入建筑设计中的“钱王祠重建工程”,北山街、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的保护整治,与杭州花圃遥遥相对,青瓦、白墙构成了独特、完善的区域小景观的盖叫天故居,还是隐藏在桃溪镇清幽山谷中的武义延福寺大殿,历史文化名城衢州市的孔氏南宗家庙……一处处古建筑,一座座遗址公园,他们在保护中努力尊重、继承和维护。充分考虑城市、乡村的历史环境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协调周边的历史格局,和谐与自然环境、人文关系,使其融为一体。在保护设计上,充分考证原有建筑构件,强调对原有古迹包括建筑及其他遗物的保护,恢复具有历史意义、城市个性的建筑形式,充分挖掘、展示历史文化资源,并有机地融入环境设计及陈列展览中。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那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作为四川文物抢修第一阶段全国技术援助单位之一,一支由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所5位专家组成的四川文物抢修技术援助队,在大地震后的第一时间赶赴四川新都,为地震中受损的宝光寺千年古塔看病——抢修新都宝光寺、杨升庵祠及桂湖、金堂瑞光塔和圣德寺白塔4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他们高超的技艺令全国同仁刮目相看。
古越大地上的文明守望者
三十春夏,三十而立——走过良渚古城,翻过越王陵,穿过大运河,已是满头白发或正茁壮成长的考古所人,实在记不清楚自己走过多少泥路,淌过多少溪流,爬过多少山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境况下,却情不自禁地说:“明天我回家。”
其实,考古队员的这句口头禅“回家”,是远指那个一辈子都安在“天当被、地当床”,早已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间——只有在井然有序的考古发掘现场,他们才真感受到“心里踏实”,真正意识到脚下那片黄褐色的土地里,凝聚着的数十万年前、数千年前、几百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存,才是他们一生一世永远不变的“情人之约”。
沐浴着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从最初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到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诞生,再到1994年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组建,一支在国内文物考古界具有强劲实力,集考古发掘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为一体的生力军,在古越大地雄起。
三十春秋,三十年轮。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史前考古、瓷窑址考古、越文化研究等优势课题和文物史迹网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硕果累累。
一串串的惊喜,带来一次次的丰收……
人们获知:良渚遗址、河姆渡遗址和龙泉窑遗址入选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新发现,反山、瑶山发掘被誉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萧山跨湖桥遗址、杭州雷峰塔、嵊州小黄山遗址、余杭良渚文化城址等考古发掘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嘉兴南河浜遗址、遂昌好川墓地获得当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
人们看见:慈溪寺龙口窑址、良渚古城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桐乡新地里遗址、海盐仙坛庙遗址、平湖庄桥坟遗址、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摘取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荣誉的无限风光。
人们品味:历年来在各项优秀勘察设计奖、文物保护规划奖等金榜提名的武义延福寺大殿、北山街历史街区、南岳忠烈祠、钱王祠、西博会工业馆、海宁盐官风情街区和盖叫天、都锦生故居的文物历史文化。
人们阅读:2001年开始,先后出版好川墓地、河姆渡、瑶山、反山、跨湖桥、南河浜、新地里、毗山、寺龙口等20余部考古报告,报告数量名列全国省级考古所前茅,质量得到国家文物局首肯和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其中《瑶山》报告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2-2003年度)专著类一等奖;《河姆渡》报告被评为第4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瑶山》、《跨湖桥》报告入选2002-2004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短短三十年,长长三十年,对永远在路上的考古所人来说,这些成就都只是转眼即失的一瞬间:跨湖桥的木舟、河姆渡的稻米、钱山漾的丝帛、良渚的玉琮、龙泉的青瓷、古塔、古庙、古民居……浙江的文明在水边诞生并源源不断地延伸着。
雨过天晴。初冬的古越大地,泥土还有几分润湿——他们依旧深情告别家人:“明天我回家。”


 未认证
未认证
 客服1
客服1